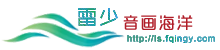- A+
光宗耀祖(一)
在公司开早会时,夏化冰接到阿姐打来的电话,说阿爸起夜上厕所中风摔倒,住进了县医院ICU,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让他赶紧带媳妇回趟老家。
等到他和小丽从两千里之外赶到病床前,夏爸已插上喉两天了,没法说话,人也处在半昏迷状态,坐在床边的阿姐正用小棉签沾水清洗阿爸眼角的眼屎,说:“不清理眼帘会沾一起,阿爸连睁眼的力气都不够了,我清楚他是吊着这一口气等你回来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对夏化冰的埋怨。看着阿姐蜡黄的脸上布满了疲惫,头发比上次见面又稀疏了许多,同岁的俩人看着至少差上十岁。
守了半天后夏爸睁开了双眼,看到他和小丽,很激动可没法说话,眼框有泪流了出来,夏化冰握着他的手,伏身在他耳边说:“阿爸,我回来了,我知道你想说啥,光宗耀祖,开枝散叶,对不对?”夏爸下巴微微的动了倆下,人也慢慢地放松平静下来,一只手反握着夏化冰的手就没再放开过。夏化冰也没敢离开半步,就这样又拖了半天,夏爸出现过两次室颤,急救室医生就把探视的人群都赶到外面,抢救了一个小时,夏爸还是走了。
等喪事办妥,把小丽先送上回广州的火车后,这么多天,夏化冰现在才算是舒了口长气,茫茫然漫无目的的走在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上,近十年间,年轻人都陆续离家去外地打工,这七线小镇连往日的那点生机都抹没了,看着到处破破烂烂的,人都见不到几个,一阵大风迎面刮来,扬起的尘土把他还算白净的脸刷成了土黄色,远处那间夏家四年前翻盖的两层红砖屋,在一群旧排房中显得很是突兀。夏化冰在裤袋里摸出一包香烟,随手点燃了一根,猛吸了几口,思续跟着吐出的烟雾拉回到从前。
夏爸是夏家三代独子,35岁那年夏妈产下了一对龙凤胎,夏化雪和夏化冰倆姐弟,“光宗耀祖,开枝散叶了!” 夏爸当时脸上笑成一朵花。大摆宴席后,整个家从此就围着夏化冰转了,倆碗面,一大一小,大碗的多数时候都加有肉或鸡蛋,小碗就是一眼瞧见的清汤挂面,阿姐小时候还会哭哭闹闹几回想抢那碗大的来吃,后来发现哭闹和抢都没起作用,也就惯性地每次捧着小碗面委屈着往嘴里扒哒,有时候,冰弟也会偷偷把肉和鸡蛋分一半在桌底下递给阿姐吃,姐弟倆感情还挺好。
俩人到了读书年纪,一起上了同一所小学,阿姐脑子灵活读书好,成绩老是排班上前两名,冰弟资质一般,学习水平就中等偏下,夏爸叹口气,嘴里叨叨心里安慰自己,男孩嘛顽皮,开化晚,大点学习就跟上来了。
夏爸在镇学校占着一个编外名额,负责看门打铃兼烧锅炉水修破门窗等一切的杂活,夏妈在家踩缝纫机接些散活,夏爸夏妈也就小学水平,可倆人都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了冰弟以后能光宗耀祖,夫妻俩靠着在学校跟老师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交情,隔三差五就往几个老师家跑,上门送点自家自留地种的新鲜蔬菜联络着感情,好让老师可以给冰弟开开小灶提高些学习成绩,平日里反复对冰弟说:“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出人头地,夏家以后就靠你光宗耀祖啦,你不能对不起祖宗。” 冰弟也从此没有了玩耍的时光,除了读书做习题,还是读书做习题。
夏爸唯一一次打冰弟是在小学五年级期间,有一次他实在困的不行,可额外的习题还没做完,就哭着说:“祖宗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不想光宗耀祖,我想睡觉。” 夏爸听了气得跳起来,抄起门边扫帚就追着他满屋子打,最终还是夏妈把夏爸拦下了。
那天晚上,冰弟摸着打肿的屁股对阿姐说:“我不想当夏家的男娃,太累了。” 阿姐白了他一眼:“我还不想当夏家的丫头呢,连肉都吃不上。” 冰弟:“要不咱倆一起离家出走吧。”阿姐:“好啊,我们去广州吧。” 当时外屋电视机上正播着一出南方城市广州背景的电视剧,说完倆人瞅着对方,捂着嘴吃吃地笑起来。
往后的许多年,夏化冰梦里不止一次地梦到过同一个场景: 他拉着阿姐的手拼命地跑,向着广州的方向跑,可都是还没跑出小镇,阿爸都会突然地窜出来,挡在他俩面前,然后一手拧起一个骂骂咧咧地抓回家去。
(未完待续)
光宗耀祖(二)
夏妈身子本来就虚,加上生产后月子没坐好,落下了病根,经常头痛和手脚渐渐地使不上劲,夏妈开头几年还会看看中医,喝些中药汤剂,一直没见啥起色,就不再舍得花钱去看病,给冰弟报课外补习班和买学习资料上却从来没吝啬过。所以中学起,阿姐就包揽了全部的家务和不时地要照顾夏妈,缺课日子慢慢变多,功课渐渐从第一名掉落到最后一名。读完初中,也和大部份女孩那样,家里舍不得花钱,高中不让上了,去菜市场打工帮人卖菜去了。冰弟高二那年,夏妈病倒了,过世前最后的话就是让冰弟专心学习,考上大学,光宗耀祖。
高考填报志愿,那个从儿时起的梦一直浅意识里影响着他,冰弟填了广州的中山大学。高考完的那天,冰弟回到家就把房门锁上了,痛快地睡了三天的饱觉,再也没人催看书做题了。无所事事的两天后,他跑去菜市场看阿姐卖菜去了,远远看着阿姐利索的身影,想着不久后可能离开看不到了,才顿觉欠阿姐太多,自己从小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被动地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夏妈和阿姐的付出,自己要如何回报才好呢。正开着小差,阿姐望到他呆愣着,就招呼他找个小板凳坐下,倆人抽空闲时分吃起一个无籽西瓜,阿姐吃着吃着突然来了句:“咦,阿爸有存那么多钱供你上大学用么?” 冰弟也给问住了:“是啊,咱家好像没那份闲钱吧?” 倆人没当过家长,一直没去想过这个问题。况且阿爸平常就是威严所在,倆人也没敢开声去问有关钱的事。
那天镇里突然响起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和咚咚的锣鼓声,是中学校长带着一群师生往夏家赶来,放榜了,冰弟是县里的新晋理科状元,夏爸兴奋地忙着与众人打着招呼,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光宗耀祖啦!光宗耀祖啦!” 冰弟从考场出来回家那天心里就有数大概率是会考上的,反倒没太大的反应,随后给几个好事的人按弄在一张大太师椅上,胸前斜挂个大大的红缎球,头上给整了个红纸折出的写着状元两个字的纸帽,被人扛拥着在镇上大街走了几个来回,阿姐脸上也发着亮光,跟着人群开心地走在冰弟一旁,笑得合不拢嘴。
晚上三人跟学校毕业班的几位老师和校长在镇里最大的饭店撮了一顿,酒足饭饱,三人回到家,冰弟给灌喝了几瓶啤酒,头晕晕的,没洗漱就回自己房间倒头就睡,半夜被尿憋醒,起床尿尿,回房时,瞟见阿姐房门开着灯也开着,见她还呆呆地坐在床头没睡。就喊了声:“阿姐咋还没睡?” 阿姐这才猛回过神,回了句:“哦,我在想妈了,睡不着,嗯,广州是个好地方,你一定要去。” 说完顺手把房门给关上了,冰弟略感阿姐神情有点怪怪的,见她关了房门,也就回房继续睡觉了。
(未完待续)
光宗耀祖(三)
那天晚上吃完饭三人回到家,等看到冰弟睡下了,夏爸敲开阿姐的房门,眼神坚定地看着阿姐说:“一定要供冰娃上完大学,我估算了下,县里教育局和学校会发些奖金,那些钱给冰娃添办些行头上学用,听校长说到了学校还可均情申请些学生补助,我存折里的钱也就够他这次的路费,第一年学杂生活费至少还缺三千。”
阿姐听到这话心急得不行,说:“当然是要上完大学啊,当然的啊,咋办啊!”
夏爸顿了顿,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马上凑齐前两年大学费用,剩下那俩年的钱我等冰娃离家了,可以跟随阿福他们去外地下小煤窑,那个来钱快些。”
阿姐问:“是啥办法?”
这次夏爸看着阿姐的眼神有点闪躲,顿了半分钟,说:“雪丫头,为了冰娃,你嫁人吧。”
“啊~~” 阿姐听了楞住了,半响才反应过来。这边的女娃好多都早早成家的,法定年龄登记结婚虽说是20岁,但大家普遍共识是双方家庭出面摆了酒席就是成婚了。登记那张纸只是官方流程走一回而已,好多等娃都生出来了才去补办登记,为的是为娃上学上户口用。阿姐今年虚岁也19了,嫁人有彩礼收,就有钱给冰弟上大学用,现在男方彩礼行情一般是四千。
看阿姐沉默着,夏爸知道她听明白了,就接着说:“有人看上你,彩礼会出到六千。”
“啊~~” 阿姐听了又楞住了,原来阿爸早就想到这个来钱法,心里有点悲哀和抵触,但想着阿爸这身子骨都打算去下煤窑了,又感觉这法子也真最顶用的。阿姐问:“对方是谁?”
“猪肉强。” 说完这话,阿爸有点不再敢看阿姐的脸,转身回房去了。
“啊~~ ”阿姐第三次楞在原地。
猪肉强在菜市场里有一个猪肉摊档,就在阿姐卖菜摊档的斜对面。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得很,今年因该有38岁上下,阿姐平时喊他声叔,菜市场里,卖肉当然比卖别的好赚钱些,阿强人挺老实本份的,开了档只管埋头剁骨切肉,闲时爱喝二两二窝头外,没别的爱好,有个老妈帮着在档边收钱吆喝。强妈相对比较强势,一般事就她做主说了算。阿姐在菜场打工也有三年了,强妈看着她也三年了,越看越满意,私底下问过阿强,阿强也是猛点头,这么利索会干活又水灵的姑娘谁又会不爱呢。强妈有次乘夏爸来买肉,拉到一旁表明想要阿姐当儿媳妇,夏爸当时口风挺紧,只说岁数上差一大截呢,没点头也没摇头,没把天聊死。等冰弟高考完,阿爸特意又上肉档买了几回肉。
这晚,阿姐就这么合衣坐在床边没睡过,想了半宿心意已定,看天有亮光,干脆起身去弄全家的早点,她敲开夏爸的房门,对夏爸说:“我嫁。” 然后俩人小声嘀咕了十多分钟,重点说的是收彩礼当学费这件事一定要先瞒着冰弟,等他到校以后找时机才告诉他结婚这档事,还有如何让强妈他们配合。
九月,冰弟顺利的到了中山大学报到,开始了第一年忙碌的大学生活,过了俩个多月,收到第一封家信,内里夹带几张喜宴照,阿姐嫁人了。冰弟又不傻,顿时明白了上学的钱是咋来的啦,这一天,冰弟第一次旷课,第一次买酒灌醉自己。。。
(未完待续)
光宗耀祖 (四)
冰弟虽说是他们县里的状元,到了大学校园,学习成绩也就是个殿底的那批,冰弟自知自己的资质,也没打算再争上游,力保不挂科就行。自从接到那封家信,大醉一场后,他就好像变了个人,除了学习外,他在学校和周边疯狂地寻找各种能省钱挣钱的杂活干。
他平时会帮有需要的男生打扫宿舍,洗衣,打饭打水,按星期收费,自己吃最便宜的饭菜,通常是踩着饭堂关门前5分钟去打饭,一般那时就剩些见底的剩饭剩菜,看多几回,饭堂师傅也领悟到他想省钱,有多剩的也一古脑全扒拉给他,象征性地收他一俩张饭票钱了事,碰到这种情况时,他吃不完的那餐就留到第二天热着对付着吃,不再来打饭了。别人扔了的衣服裤子看着合身的也捡来穿,星期天一整天在校外一个中学课外补习班兼职教学生高数。
这样过了大半年,学生第二小饭堂承包给了一家姓刘的家庭,饭菜花样是更多更好了,但价格也上调了。冰弟心里直骂娘,但凭学生饭卡吃饭,再贵也比在外吃便宜,他有时一天就打一餐吃,这天又是最后一个去打饭,瞧见刘老板在卸货,看着他脚好像崴着了,一瘸一瘸的,他赶紧跑上去帮手卸完了货,完了自荐可以来当小工,有杂活多时就帮手干干,刘老板说小本生意请不起,冰弟忙说不收工钱,宿舍就在不远,需要帮手时打个招呼就可以来,很方便,有活干那天就管俩份饭就行,刘老板当时确实需要个帮手,就答应了下来,这样冰弟的吃饭大问题也算解决了一半。
刘老板一家6口人,三代同堂,刘老头刘老太身体硬朗,在饭堂摘菜分菜打下手,刘老板夫妻俩天蒙蒙光就起床,踩着三轮车去郊区早市菜场进货,回来就忙着掌厨,还有一个20岁的女儿小丽,一个上初中的小儿子。小丽是个开朗爱笑的姑娘,高中毕业后就在饭堂帮手干活了,早点一般就留小丽来操办,5个大蒸锅齐上,忙而不乱,全家人齐心齐力,分工合作,是勤劳和睦温馨的一家子。小丽跟冰弟接触多了,俩人也生出了不一样的情愫,刘老板一家跟冰弟也渐渐自然地处成了一家人。
冰弟两年寒暑假都没回家过,明面上是因为阿姐嫁了人,阿爸在外地下煤窑,回家也是他一个人呆着,来回还要花上不少的路费钱,太不划算了。其实最主要还是学费的来源问题,他心里这道坎过不去。
第三年阿姐生了个儿子,冰弟总算回家了一趟,这时侯的他已没有了以往的天真和青涩,身材样貌都变了许多,在家呆了三天时间,吃完满月酒,临走时把六千元包在红包里硬塞回给阿姐,还塞回给阿爸寄去的三千元,让阿爸别去下煤窑了,别再寄钱了,做完这些,就匆匆忙忙又赶回学校了。
又过了五年,冰弟寄了一笔钱回去,让阿爸找人翻新家里的老房子,他过半年后会带个媳妇回家摆酒。阿爸激动得三天都没睡,找人两个月就把旧房推倒翻了新。摆酒席那天,热闹非常,全镇的人都知晓这喜事,是夏爸最风光的一天,笑容像被雕刻在脸上,没变动过。冰弟觉得他该做的事都做完了,第三天就推说公司忙,带着小丽回了广州。过后冰弟也很少回家,但每月的电话不间断,逢年过节也会寄些钱回家。
冰弟抽完烟,朝阿姐家走去,阿爸过世了,剩下的房子得办手续过户给阿姐,走到门口不远处,就听到男孩的哭喊声:“我不要光宗耀祖。。。我不要光宗耀祖。。你们再生个让他光宗耀祖吧。。”
(完)